(一)贷款人的义务与解除权
1、“贷款义务”的法性质
2、贷款人的有限解除权
(二)借款人的义务
1、“借款义务”
2、还款义务的发生时点
七、证明责任
(一)贷款人的举证
(二)无书面借款合同的特别规定
规范目的与内容沿革
(一)规范目的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679条的规范目的在于将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规定为典型的要物合同,即以借款的提供作为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成立要件。由此,无利息的自然人借款为单务无偿合同,而附利息的自然人借款则为单务有偿合同。
【2】规定自然人借款合同要物性的目的被认为是强化对自然人借款意思表示的干预,维护金融秩序,体现互助的伦理性,并有利于“减少不必要的纠纷,促进市场交易便捷”。[1] 申言之,之所以将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规定为要物合同,是因为自然人之间借款通常数额有限,且通常具有亲友关系;自然人之间的借款不存在金融机构所必需的复杂程序;自然人通常并非专业人士,要给予一定的思考时间;自然人之间往往具有互助、无偿的性质。[2]此外,自然人借款对金融秩序的影响是较为有限的,[3]要物性所带来的交易上的不便利并不会对金融交易产生整体性的妨碍。因此,第679条为作为贷款人的自然人提供了保护,使得贷款人得以在借款交付之前否定其提供借款的意思表示,即对自然人借款合同中的意思表示效力做弱化处理。
【3】本条仅适用于借款合同双方均为自然人的情形,[4]延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原《合同法》”)以来的“主体规制”的立法思路。[5]
(二)内容沿革
【4】在《民法典》生效之前,原《合同法》第210条将“贷款人提供借款”作为自然人借款合同的生效要件;这被认为是缓和要物性的规定。[6]但当时的立法参与者并没有区分成立要件与生效要件的明确意识,而是认为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当然地属于要物合同。[7]《民法典》制定过程中,立法参与者认为原《合同法》第210条的“本意”是将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规定为要物合同,但条文的表述容易产生自然人借款为诺成合同的误解;为避免争议的延续,“贷款人提供借款”被修改为成立要件,这样也能与定金合同及无偿保管合同的规定保持一致。[8]
【5】从字面上看,条文内容的变化是比较显著的,成立要件与生效要件在法性质上有着截然的区分;但上述变化并未影响司法裁判的连续性(边码60)。
规范性质与射程
(一)规范性质
【6】《民法典》第679条是关于合同成立要件的规定,会被当然地认为属于强制性规范的范畴,学说上通常也是这样认为的。[9]但是,从立法政策上看,第679条重视的是贷款人的自发性,若贷款人的自发性已经获得充分的表达,并且当事人自愿订立诺成的借款合同,此时承认诺成的自然人借款合同反而是对贷款人自发性的尊重。
【7】从强制性规范的趣旨来看,除了保护特定的当事人,还可能涉及第三人保护或者是公序良俗的维护。[10]第679条的立法政策主要是为了保护贷款人,并没有第三人保护与善良风俗方面的特别考虑。而且,自然人之间的借款被认为是不会破坏经济秩序的,[11]于公序的影响十分有限。可见,贷款人“深思熟虑”地放弃保护是没有问题的。
【8】另一个可能的视角是重新考虑典型合同的意义。由于契约自由原则的存在,合同的具体类型是无限的,有关典型合同的法规范应被理解为裁判规范,并不妨碍当事人创设民法未规定的合同类型。[12]学者指出,合同的性质决定不是单一层次的,而是多层次构成的。[13]作为典型合同的借款合同之下,存在着金融机构借款和自然人借款的下层分类。自然人借款还进一步可以区分为无偿自然人借款和有偿自然人借款,后者还可以在民商二元的基础上继续地区分出民事自然人借款、商事意图的自然人借款的子类型。不同层次与类型的借款合同在规范适用方面是存在差异的。在当事人明确排斥典型合同规范适用的场合,只要无涉公序良俗,应当承认当事人意思的效力。
【9】因此,在本文的立场上,《民法典》第679条属于“半强制性”规范:若作为当事人的自然人在典型合同的意义上订立借款合同,则以借款的提供为成立要件;若当事人订立的是非典型的借款合同,则自然应当尊重当事人的意思,从而可以采取诺成的方式。[14]说到底,这仍然是一个有关合同解释的问题。[15]
(二)规范射程
1、民事自然人借款的适用
【10】从目前的比较法趋势来看,《民法典》第679条将自然人借款合同在文义上规定为纯粹的要物合同是比较独特的立法例。虽然罗马法以来的传统是将借款合同作为要物合同来对待的,[16]近代民法典也普遍延续了这一立场;[17]但要物合同的诺成化是近年来比较法及示范法(软法)领域较为显著的趋势。[18]学说上也普遍认为借款合同的要物性是罗马法的历史残留,在合同原则上采诺成主义的背景下,并没有保留要物性的必要。[19]
【11】我国学说上,对于自然人借款合同的要物性也多有诟病。有观点认为自然人借款合同要物性的正当性基础在于尊重无偿行为的自发性,从而应当对第679条的适用范围做出限缩解释,即仅适用于无偿的自然人借款合同,而有偿的自然人借款应认定为诺成合同。[20]这样的解释论立场在原《合同法》时期就存在,其根据是较为典型的“有偿、无偿行为二元论”。[21]还有观点认为要物契约仅具有知识考古意味,在债务合同层面已经失去意义,应当摒弃该概念。[22]
【12】如果把合同看作当事人自己决定的产物,无论有偿还是无偿,其拘束力来源都是当事人的意思,即便无偿也不需要做特别的处理。[23]既有的有偿、无偿二元论具有客观归责的意味,与私法自治的基础原则有所龃龉。正如立法参与者所指出的,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具有亲友关系、互助的特征,而亲友间的互助是带有交换性的。若跳脱对待给付来理解无偿,则应当将具体借款合同纳入连续性的交换或给付“关系”中予以理解,个别借款是否附有利息是无关紧要的。[24]
【13】此时,最重要的仍然是当事人的意思,即判定当事人具有借款的法效意思。本条所规定的要物性,实际上是以借款的提供作为当事人法效意思的确认,从而将构成法律行为的自然人借款与情谊行为区分开来。换言之,《民法典》第679条之所以规定要物性,是要在作为社会现象的自然人借款中框定民法规范的对象。需要说明的是,此时的自然人借款仍然保留亲友间、小额、无偿或低息的预设特征,本文称之为“民事自然人借款”。
【14】作为例外,若自然人之间存在以诺成的方式来订立借款合同的合意,那么基于本文对于《民法典》第679条法性质的判断,也将排除本条的适用。
2、商事意图的自然人借款的例外
【15】然而,有趣的是,立法参与者有关规范目的的判断仅仅是原《合同法》立法、乃至更早时期的经验法则的简单重述;[25]况且,这样的经验法则目前并未得到任何实证数据的支持,很可能只是来自于早先的个体感性认知。就当下的情形以及未来的趋势而言,基于友谊的小额借贷并没有显著的意义——人们已经可以在网络平台上轻易实现短期小额借款。在这样的背景下,自然人之间的借款的社会重要性已经大大降低了。
【16】出现在实际讼争中的自然人借款则往往并不属于立法参与者所设想的情形,借款主题虽然是自然人,但其借款的用途通常是用于生产经营或其他营利目的,且数额显然超越一般的生活需要;通常附带担保也是此类借款的显著特征。本文称该类型的自然人借款合同为“商事意图的自然人借款”。[26]由此而生的问题在于:商事意图的自然人借款是否仍然是要物合同?
【17】此时,若仍然坚持自然人借款合同的要物性,则会在实践层面造成明显的障碍。在贷款人要求借款人为借款提供担保的场合,实践中贷款人通常是在签订借款合同和保证合同后才提供借款的。[27]若借款合同为要物合同,那么提供借款前设定的担保均是无效的,因为作为主合同的借款合同尚未成立。对此,没有迹象表明立法者作出了明确的判断。实务中,有借款人因此主张担保的无效,但法院却对此避而不谈。[28]
【18】比较法上,规定借款合同要物性的日本民法在颁行的不久之后就出现了上述问题。对此,实务操作采取了做成借贷证书、然后再办理抵押的迂回手段;学说上则普遍认为应当承认诺成的借款合同的有效性。[29]
【19】近来,区分民事、商事借款合同而分别予以规范的学说渐次出现。[30]虽然由于缺乏明确的商事法律规范,法院不得不将第679条作为处理所有类型的自然人借款的“一般条款”,但法院通常并不纠缠于借款合同的要物性,也不会因为担保的提供在借款交付之前就否定担保的效力。可见,裁判实务也或明或暗地在努力消除要物性对市场交易的阻碍。具有商事意图的自然人借款显然与立法参与者的设想不同,解释上可以将其排除在第679条的射程之外。但考虑到当下理论与实务的状况,本文将商事意图的自然人借款作为第679条规定的要物性的“部分例外”(边码39)。
【20】至于商事意图的自然人借款的判定,借款的数额应当是最为重要的因素。凡是数额处于日常生活需要范畴内的借款,原则上均应推定为民事自然人借款;超越日常生活需要的,则应推定为商事意图的自然人借款。[31]同时,若自然人借款附有担保,则也应当被推定为商事意图的自然人借款。当然,以上因素是判断自然人借款的缔约目的的外在因素,主观目的才是区分民事与商事意图的自然人借款的根本依据。[32]
民事自然人借款合同的成立要件
【21】本条仅规定了贷款人提供借款时借款合同成立,并未明确规定当事人之间须存在借款的合意。但即便是要物合同,从逻辑上说,当事人在实际提供借款之前必然会有借款的合意(在先借款合意)。相对于诺成合同,本条只是增加了“借款的提供”作为特别的成立要件。因此,本条包括当事人的“在先借款合意”以及“借款的提供”两方面的要件;实务中也有如此理解的案例。[33]
【22】但根据本条的规定,在民事自然人借款的场合,当事人之间的合意并不会产生借款合同层面的法律效果。而要在借款合同层面发生法律效果,则需要借款人提供借款,因此以下的论述将集中于“借款的提供”这一要件。[34]而第679条所规定的“提供”,则被立法参与者理解为“交付”。[35]
(一)提供的当事人
【23】根据在先借款合意以及合同相对性的原理,原则上应当由贷款人向借款人交付借款。但在贷款人委托第三人向借款人提供借款的场合,法院也承认借款合同的成立;其理由在于,借款的提供形式不会实质上影响借贷法律关系的成立。[36]有法院指出,“实践中也大量存在出借人委托他人或利用他人账户代为转款,履行提供出借款项之义务的情况”。[37]
【24】借款的受领人方面,借款人以外,贷款人向在先借款合意约定的第三人托收账号转入借款的,法院认为已经构成借款的提供。[38]向约定的第三人(借款人的债权人)支付款项的,也会被法院认定构成借款的提供。[39]
【25】在第三人接受借款人委托向贷款人借款但未披露借款人的案例中,贷款人向第三人提供了借款,第三人将借款转交借款人;第三人主张此时在贷款人与第三人、第三人与借款人之间成立两个独立的借款合同。对此,法院认为因第三人未实际提供借款,借款合同在贷款人与借款人之间成立。[40]
【26】在共同借款人之间有合伙关系之时,若贷款人向共同借款人之一提供借款,也会被认为已提供了借款。[41]
(二)现实提供
【27】《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年12月第二次修正)(以下简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二次修正)”)第9条规定了贷款人提供借款的典型情形,包括现金支付、银行转账或网上电子汇款、票据交付、移交特定资金账户支配权等。
【28】在现金交付借款的情形,提供的标的物应当为在先借款合意约定的币种。在约定不明的场合,贷款人向借款人交付了“虚拟货币”;法院认为虚拟货币不具有法定货币属性,从而否定了贷款人已经提供借款的主张。[42]
【29】以银行转账、网上电子汇款等形式支付的,司法解释认定的标准为“资金到达借款人账户时”;实务中也有法院采取“汇入”的表达。[43]最高人民法院在裁判中指出,“款项到达借款人账户”指的是“借款人能够实际控制该账户或者出借人能够证明借款人与收款账户存在相关经济往来”。[44]在金融机构借款的案例中,法院对于贷款金融机构将借款汇入借款人账户后又划扣的行为,认为借款人没有取得对账户内款项的实际控制,从而认为贷款人并未提供借款。[45]
所谓的“到达”,在民法的语境中通常指的是意思表示进入受领人的控制领域。[46]由于账户内的资金是没有物理实体的,所以无法实现事实上的控制,需要根据转账或汇款的具体构成来确定“到达”的含义。
无论是通过银行还是第三方支付平台进行转账和汇款,实际上都涉及多方交易关系。通过银行交易的场合,贷款人与汇出行签订汇款合同,再由汇出行与汇入行根据合作协议进行结算,最后由借款人根据其与汇入行的用户协议提出支付请求(汇出行与汇入行可以为同一银行);第三方支付的情形也是类似的,只是在汇出行与汇入行之间接入了第三方支付平台。关于贷款人与汇出行签订的汇款合同是否构成第三人利益合同,学说上存在争议。[47]但该合同目的在于向借款人支付款项,借款人的账户金额实现正增长并且借款人可以利用账户资金,应属于《民法典》第522条规定的第三人利益合同。
基于贷款人与汇出行签订的汇款合同,汇出行的债务内容是通过结算系统向汇入行的特定账户转账。借款人要行使账户权利,须依据其与汇入行的用户协议来提取或转移资金,汇入行并不对借款人承担上述第三人利益合同上的债务。[48]因此,根据上述第三人利益合同的债务内容,资金被计入借款人在汇入行的账户时,即为“到达”。若借款人与汇入行之间存在特定欠款事由,汇入行划扣其资金或借款人在汇入行的账户权利被限制行使的,并不影响贷款人提供借款的认定。因此,从规范意义上来说,“到达”是指借款人具有行使账户权利的法律上可能性成就时。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如果是以ATM机进行转账或汇款的,则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支付结算管理防范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有关事项的通知》(银发〔2016〕261号)的规定,借款人行使账户权利存在延时24小时的可能,即记入账户后24小时方为“到达”。但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加强支付结算管理防范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有关事项的通知》(银发〔2019〕85号)进一步规定,延时规定不适用于用户选择“实时到账”的情形。
【30】自然人借款的场合,使用票据交付借款的情形并不多见。与转账的情形类似,以票据交付借款的,司法解释中的“自借款人依法取得票据权利时”应被理解为“借款人具有行使票据权利的法律上可能”。在借款人受领贷款人提供的本票后背书给第三人的场合,法院认为贷款人已实际提供借款。[49]
“票据”的范畴不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所规定的范围,以交付具有流通性的无记名债权凭证来提供借款的,也应在当事人之间成立借款合同。[50]
【31】在以特定资金账户支配权来提供借款的情形,法院认为贷款人将银行卡交付借款人并告知密码的,构成借款的提供。[51]在解释上,此种情形也属于借款人具有行使账户权利的法律上可能性。
实务中存在以信用卡账户支配权提供借款的例子。[52]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银行账户管理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规定,信用卡账户出借本身具有违法性。如果承认其违法性,则交付信用卡并告知密码的场合,借款人是不具有行使账户权利的法律上可能性的。但涉及自然人借款合同的案件中,法院通常对此不做判断。此时,自然人借款对金融秩序的影响较小可以用来说明法院的立场;也可以认为上述有关信用卡的规定属于管制性规定,与民事行为效力无涉。[53]
【32】需要指出的是,除以现金方式提供借款外,司法解释所规定的多样提供方式实际上是对自然人借款合同要物性的缓和。在贷款人没有现实地交付标的物(金钱)的场合,也能够认为第679条规定的要物性得到了满足。[54]但最高人民法院的主要意图仅在于明确自然人借款合同的成立时点,并未意识到与要物性之间的关联。[55]
(三)观念提供
【33】借款人的还款义务是以获得借款为前提的,因此原则上无法采取观念提供的方式。但在买受人赊购的场合,若当事人事后合意将货物价款转换为借款,则不需要借款的现实提供。[56]此类因其他债务转换而来的借款被称为“准借款”,仅凭合意就会导致原债务的消灭及借款债务的发生。[57]
在对既存债务进行清理而重新出具借据的情形,虽然形式上当事人重新订立了借款合同,但实际上是对既存债务的确认。[58]此时,无需考虑是否存在提供借款或观念提供的问题。
【34】另外,在贷款人向借款人提供贷款人对第三人的金钱债权以替代现实提供之时,由于此种情形当事人必然存在明确约定,因此须根据当事人合意的内容来确定“贷款人提供借款”的时点。若不存在明确约定,则应比照债权让与的规定,借款人对第三人得以行使权利时(对抗第三人的要件满足时)即为借款提供时。
【35】实际上,在以特定资金账户支配权来提供借款的场合,贷款人给付借款人的就是贷款人对第三人(特定金融机构)的债权。例外的是,此时并不需要具备对抗第三人的要件。当下自然人资金账户交易普遍采取“凭密码”方式,借款人持卡并输入正确密码的话,银行向借款人付款构成“向债权准占有人清偿”,[59]无需考虑债权让与的构成。
(四)提供借款的“提供”[60]
【36】贷款人应按照在先借款合意全额提供借款。贷款人交付票面金额与合意数额一致的票据时,若到期即可全额兑付但借款人采取贴现等方式获得“比例”现金时,应认为借款合同的金额为约定全额。[61]
【37】贷款人部分提供借款的,不影响最终借款合意的成立。由于借款的提供并非是履行合同约定的金钱给付义务,而是以此来成立借款合同,因此“部分清偿不构成有效清偿”的规则不适用于该场合。根据《民法典》第670条,以实际提供金额为本息计算的根据。
【38】此外,借款原则上应现实提供,不得采取口头提供的方式;在先借款合意约定由借款人“往取”借款的情形则为例外。
商事意图的自然人借款合同的成立要件
【39】若将商事意图的自然人借款的情形纳入《民法典》第679条反对解释的范畴,则商事意图的自然人借款合同的成立直接适用《民法典》第483条即可。但考虑到当下裁判实务普遍以第679条作为所有类型的自然人借款的成立规范,以下的解释将以不脱离裁判状况为前提。由此,提供借款仍然是商事意图的自然人借款的成立要件,只是当事人的在先借款合意会成为借款合同最终合意的第一阶段,而提供借款为最终合意的第二阶段。这样的立场可以被称为“二阶段合意”论,其重心在于对在先借款合意的讨论。
(一)在先借款合意的有效性
【40】 “在先借款合意”指的是当事人就以贷款人提供借款的方式成立借款合同达成的合意。[62]如果坚持要物合同的法性质,自然人借款中的在先借款合意只是合同的成立要件之一。但是,从逻辑顺序上看,上述两要件是继起的关系,即借款合意在先、借款提供在后。此时的问题就在于在先借款合意与借款提供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41】裁判实务是承认在先借款合意的“预约”性质的,尤其是在金融机构借款的场合。金融机构与借款人订立的《最高额信贷合同》、[63]《个人授信协议》、[64]《个人授信及担保协议》[65]等会被法院认定为借款的预约。在民间借贷的诉讼中也存在类似的案例。[66]
然而,即使是不自觉地,裁判实务普遍肯定了自然人在先借款合意的法律效力。在某一案件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贷款人提供借款的行为“履行了《借款协议》中约定的出借义务”。[67]根据当时的原《合同法》的规定,基于合意的《借款协议》在贷款人提供借款前并不导致借款合同的生效,所谓“出借义务”的正当性基础只能是合意达成的《借款协议》的有效性。类似的,最高人民法院在近来的裁判中认为自然人借款的贷款人提供借款是“依约”履行的,[68]此时的“约”只可能是当事人在先的借款合意。
(二)在先借款合意的法性质
【42】对于以上裁判现象,可能的解释之一就是将当事人在先借款合意认定为自然人借款合同的“预约”。
【43】问题在于,预约概念的有用性本身就值得怀疑。学者指出,德国法上预约概念的产生是为了缓和要物合同的要物性。随着德国债法改革对要物合同的诺成化,[69]德国学说与实务上对于预约都存在较大的质疑;德国法院则倾向于通过认定为附条件的行为来规避“预约”。[70]而预约制度在意大利的确立和发展,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弥补缔约过失责任的不足;以及缓和合意物权变动的效果。[71]中国民法并无上述语境,预约的制度价值需要重新的考虑。
【44】我国《民法典》第495条规定的预约并不当然包含直接请求履行本约的效力,[72]代表性的学说也认为违反预约合同的违约责任应当根据案件具体情况予以认定。[73]一旦预约与本约之间的关联被割裂或稀释,预约制度的必要性就大大减损了。而若预约能产生履行本约的请求权,则贷款人根据预约承担成立本约的义务,即承担“提供借款”的义务——自然人借款合同的要物性就此荡然无存。
【45】学者正确地指出,预约的标的在于另一合同的订立而并非直接的财产流转。[74]根据合同拘束力理论,只要考虑预约合同所约定的债务的拘束范围和强度就足够了,没有必要考虑后一合同的债务内容。因此,在本文的立场上,预约概念是描述性的,是为说明和理解上便利而采用的便宜说法。
【46】如果“借款合同的预约”的解释不成立,另一种可能的解释就是直接承认借款合意的效力,而将贷款人提供借款解释为成立或生效所附的停止条件。这样也能说明司法裁判对于在先借款合同效力的认可。但是,正如学者所指出的,若将标的物交付作为停止条件,这对于需要提供借款的贷款人来说构成了“纯粹随意条件”。[75]而纯粹随意条件的成就完全取决于一方当事人的主观意愿,在合同的成立方面是没有意义的。[76]因此,将借款的提供视为停止条件的观点也无法成立。
【47】基于在先借款合意与借款提供的继起关系,可以将在先借款合意视为最终借款合同的中间合意。任何一个合同的缔结,总是要经过开始缔约接触到最终形成合意的过程,时间和空间跨度会使谈判内容的复杂程度发生变化。[77]由此,合意的最终形成是渐进的、逐步成熟的过程。学者认为,谈判阶段的合意应分为“应进行交涉的合意”与“包含未决定条款的合意”;前者达成的场合,当事人承担应诚实交涉的义务。[78]从在先借款合意到最终借款合意,仅需贷款人提供借款,即贷款人应促成最终合意的达成。因此,作为中间合意的在先借款合意应界定为具有独立意味的“应进行交涉的合意”。
(三)在先借款合意的法效果:贷款义务
【48】立法参与者认为,只要不存在借款的提供,即使当事人订立了借款合同,借款人也无权请求贷款人履行或承担不提供借款的违约责任。[79]很显然,上述表达中的“借款合同”指的是在先借款合意。但这样的观点并不能说明司法裁判的普遍状况。
【49】而根据前文的论述,无论采取以上何种解释立场,只要承认在先借款合意的有效性,则贷款人就须根据在先合意承担提供借款的义务(“贷款义务”)——自然人借款合同的要物性就需要另外的理解了(边码64、65)。
【50】若在先借款合意已成立,借款人应有权请求贷款人提供借款。若贷款人未实际提供借款,那么借款人基于在先借款合意就可以请求其承担在先借款合意层面的违约责任。只要承认在先借款合意的独立性,原则上《民法典》合同编通则所规定的违约责任形式此时均可适用。
【51】有观点认为,在有偿的自然人借款场合,若贷款人“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故意不提供借款”的,应承担缔约过失责任。[80]贷款人不提供借款而导致最终贷款合意无法成立的情形属于《民法典》第500条所处理的事实对象,并不在本条的射程之内。而且,无偿的自然人借款中出现上述情形的话,仍然有缔约过失责任的适用可能,《民法典》第500条被规定于合同编总则部分,应一体适用于所有合同。[81]
需要说明的是,在判断缔约过失责任的场合,有偿、无偿的区分并非毫无意义。对信赖的保护被认为是诚信原则的必然体现,[82]而有偿或无偿可以被当作认定信赖是否合理以及合理性程度的因素之一。
【52】若承认在先借款合意的独立意味,为了担保最终借款合意的成立,当事人可以就贷款人提供借款的债务设定担保。
【53】若提供借款是贷款人的义务,那么借款人就有请求贷款人提供借款的权利。此时,就会产生借款人能否将该权利让与第三人、以及贷款人能否将该义务转由第三人承担的问题。
借款法律关系中,借款人的资力和信用状况对于贷款人能否最终回收借款是极为重要的。正如前述,虽然在先借款合意具有独立的意味,但其只是整个借款合同的阶段性合意,其产生的合同上权利应当被置于整体借款法律关系中予以观察。虽然是交付金钱的义务,但提供借款是作为订立典型意义上的自然人借款合同的必要条件,其目的不在于金钱价值的移转,而是合同的订立,因此并不属于第545条第2款所规定的“金钱债务”。考虑请求贷款人提供借款的债权与特定当事人的关联,应认定其为不可让与的债权。
对此,日本法上的多数说及判例都认为,消费借贷中的请求交付标的物的权利是不得单独让与的;少数说虽然认为可以单独让与,但消费借贷仍然在贷款人和原借款人之间成立。[83]
以否定让与可能性为前提,借款人请求贷款人提供借款的权利也无法出质。
【54】通常情况下,债务承担需要取得债权人的承诺。但是,在贷款义务的场合,谁提供贷款实际上对借款人来说并不重要,因此原则上以上债务的承担不需要借款人的同意。此时也存在较为折衷的解释可能,就是在未取得借款人承诺时,贷款人将贷款义务交由第三人承担并履行的,仍然在原贷款人与借款人之间成立借款合同。
自然人借款合同的当事人被认为往往存在一定的基础关系,由此会产生一定的信赖关系。即便此种信赖无法达到被法律所承认的强度,但至少也应被当作社会现象而给予一定的尊重。基于这样的考虑,在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未取得借款人承诺而发生债务承担的,应被解释为“履行承担”,[84]并不改变借款合意的当事人。
【55】因此,在有在先借款合意或者当事人采诺成借款合同的场合,贷款义务及相应的借款人权利的移转规则与通常的债权让与、债务承担是逆向的。这是借款合同颇具趣味的地方。
合同成立:还款义务的要物性
【56】正如前述,将自然人借款合同认定为要物合同的正当性已受到极大的质疑;以上“二阶段合意”的解释构造也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自然人借款合同的要物性。但《民法典》的规定与立法者的意图是非常明确的,代表性的观点也支持要物合同的立场,解释论层面无法对此视而不见。另外,迄今为止的批判观点主要是基于要物合同的概念仅具有“历史正当性”的,如果能在“现实正当性”层面对自然人借款合同的要物性作出说明,解释论就不会过分偏离法规的文义。
(一)借款合同的“成立”
【57】第679条规定的法效果是“借款合同成立”。所谓合同的成立,正如学者所指出的,是一个事实判断的问题,于此相关的生效则是价值判断。[85]有观点认为区分法律行为的成立与生效是正当的,兼顾了意思主义与表示主义,同时突破了民法通则对民事法律行为“合法性”的限定。[86]否定区分的观点则认为,成立与生效的区分只有在附条件和期限合同等成立与生效分离的场合才有意义。[87]
【58】第679条区分了合同的成立与生效,但根据《民法典》第136条的规定,法律行为的成立与生效原则上是对同一事实的不同叙述,时空上缺乏分割的界限,因此否定区分的立场值得赞同。当事人之间存在合意,合同即告成立,若当事人对效力发生有特别的约定,从其约定即可。说到底,这还是一个意思表示解释的问题。
【59】近来有观点则认为,应当区分“成立、生效、效果”,重视法律效果层面的具体变动。[88]抽象地谈合同成立或生效并没有实际的意味,应当在权利义务变动的层面考虑具体的效果。因此,本条所规定的“借款合同成立”,在当事人没有特约的情况下,在解释论上应理解为当事人合同上义务的发生。
对于要物的自然人借款合同来说,由于贷款人提供借款是最终借款合意的成立要件,提供了借款的贷款人并不承担合同上义务。因此,自然人借款合同上的义务仅指向借款人还款义务,借款合同成立即意味着还款义务的发生。
【60】而就裁判实务来说,“成立”或“生效”的理论区分在法院判决中并没有受到重视。在原《合同法》有效的时期,就有法院将“贷款人提供借款”认定为自然人借款合同的“成立要件”,而非原《合同法》第210所规定的“生效要件”。[89]也有法院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成立”作为说理的“序章”。[90]还有法院把贷款人提供借款理解为自然人借款合同的成立及生效要件。[91]甚至有法院在引用原《合同法》第210条时,直接把其中的“生效”改为“成立”。[92]实际上,最高人民法院也并未明确区分成立与生效,而是认为合意加上借款交付的事实就能导致借款合同的“成立及生效”。[93]在《民法典》生效之后,仍然有法院认定借款合同因“贷款人提供借款”而“合法有效”(即为生效要件)。[94]
(二)还款义务的要物性
【61】若第679条规定的“成立”指向借款人还款义务的发生,那么维持要物性的立法意图如何体现?对于要物性的历史合理性,学说和比较法上的批判已经非常充分。但是,在中国法的语境中,是否存在历史因素以外的合理性,仍然是需要说明的问题。
【62】对于以上问题,就要物性同样抱有质疑的日本法可资参考。日本通说认为,消费借贷的要物性体现为返还义务的发生以标的物的交付为前提。若没有标的物交付就承认返还义务的发生,是违反常识的认定。[95]此时,并非消费借贷的合同成立或生效具有要物性,而是返还义务的发生是要物的。
【63】学者指出,之所以返还义务具有要物性,是基于消费借贷不同于使用借贷或租赁的特定性质。后者的场合,出借标的物的当事人并不会丧失处分权,而消费借贷的贷与人则会因交付而丧失标的物的处分权。作为替代,贷与人此时就能取得对借用人的返还请求权,这是在实质上妥当的思考路径。[96]
【64】以上的观点并非是在成立与生效的层面来讨论自然人借款合同的要物性,而是在法效果层面来考虑要物性在民法语境的具体意味。所谓的要物合同,在现代法的语境中,也可以理解为以法定交付方式来表明合意成立的合同。这样的理解一定程度上可以摆脱“要物性是历史残留”的指摘,但却会在实际上否定要物性规定的必要:不如率直地规定为要式行为。可见,无法仅仅抽象地在成立或生效层面讨论自然人借款合同的要物性。
而从合同具体内容上来看,学者指出,消费借贷应作为“以物的返还为目的的契约类型”进行整体的把握,返还义务是该契约的本质要素,返还义务不发生的话,也就没有必要承认契约的成立。[97]解释论上,可以将自然人借款中的借款人义务强度认定为受领借款后履行还款义务,这可以通过将缔约目的纳入债务内容的补充解释予以实现。就此而言,第679条立法意图中的要物性还体现为还款义务的要物性。
【65】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将要物性与还款义务发生相关联的观点,很大程度上是以消费借贷合同为预设对象的。我国民法中并没有作为有名合同的消费借贷,而仅仅规定了其中的借款。由于金钱的强制流通性,消费借贷中的“返还原物”的交易目的在借款合同中并不显著;基于借款合同而返还的并非原物,而是与原物在流通上没有差异的等价物。因此,将第679条的要物性归结到还款义务的发生,一方面是在不过分背离文义的前提下,对规范作出尽量合理的解释;另一方面则意在将关于借款合同的规定作为有关消费借贷的一般法,准用于借用等无名合同。
诺成的自然人借款合同
【66】按照本文的立场,要物的自然人借款是第679条意义上的典型合同,而贷款人与借款人可以合意采取诺成的方式来订立非典型的自然人借款合同。[98]合意达成后,贷款人即负有提供借款的义务,而借款人则承担还款的义务。但由于借款人使用借款的对价并非还款,而是支付利息,因此上述两义务之间不存在对价上的牵连关系。[99]
【67】当事人是否具有以诺成方式来订立借款合同的意思,则是意思表示解释的问题。较为便利的做法是,根据《民法典》第668条的规定,未采取书面方式的自然人借款可推定为要物合同,而采取书面形式的自然人借款合同则有解释为诺成合同的可能。[100]日本债法修订后,现行法就是将书面的借款规定为诺成合同的。
【68】另外,以上解释论层面的推定是可以通过对当事人意思的认定来反证的。合同法所规定的签字、盖章等都应原则上理解为任意性规定,而不是强制性规定,都是辅助法院来认定合意是否存在的。对于形式要件,原则上也应如此理解;[101]除非有涉及公序良俗的政策目的。根据《民法典》第490条第2款,履行行为可以补正书面形式方面的瑕疵,可见有关形式要件的规定并非绝对的强制性规范,应被视为合同解释的依据之一。
(一)贷款人的义务与解除权
1、“贷款义务”的法性质
【69】此时,“贷款义务”不再是最终借款合同的成立要件,其法性质为对诺成借款合同的“履行”,从而为纯粹的金钱给付债务。《民法典》第545条规定第2款赋予金钱债权强制流通性,不受当事人禁止让与特约的限制,其理由在于金钱债权让与对债务人所造成的影响较小。[102]诺成的自然人借款合同场合,贷款义务作为借款人的金钱债权,其让与不影响借款人的还款义务,因此得适用第545条第2款。[103]
2、贷款人的有限解除权
【70】在立法论层面,有观点认为,在诺成的无偿借款场合课以贷款人提供借款的义务是不恰当的,应参照赠与规范的趣旨,赋予无偿借款的贷款人在履行提供借款义务之前的解除权。这样的观点立足于日本民法关于赠与合同形式的区分,主张已作成书面形式的无偿借款排除上述解除权的适用,因为书面形式已经表明了贷款人的自觉。[104]还有学者指出,同样为无偿的合同,自然人借款合同的要物性与赠与合同的诺成性在体系上是矛盾的,立法论上有规定贷款人任意撤销权的必要。[105]
【71】逻辑上看,无息借款当然不会被认为属于典型合同意义上的赠与,因为其缺乏受赠人财产增加、赠与人财产减少的实质要素。[106]但当事人的缔约目的在于使得受领人无偿获得特定期间内的资金使用利益之时,贷款人可以通过提供无偿或利息显著过低的借款来实现上述目的。此时,最重要的是赠与意思的判断。
所谓“赠与意思”,应大致理解为“具有使他人受利益的目的”。[107]一旦具有该意思,无息或显著低息的借款合同就具有了赠与合同的性质(“准赠与”),就有可能准用赠与人的任意解除权。[108]当然,这不是因为借款的无偿性,而是因为此时的借款属于现实类型的赠与合同。[109]
【72】另一个有关问题在于,贷款人能否主张类似于赠与人的穷困抗辩(《民法典》第666条)来拒绝履行提供借款的义务。借款合同具有准赠与性质的场合,《民法典》第666条自然有适用的可能。
【73】另外,日本民法第587条之2第3项规定,借款人受领之前当事人一方进入破产程序的,诺成借款合同即失去效力。从保护贷款人的规范目的来看,我国法上的自然人借款也应做类似的解释。借款人丧失资力会导致贷款债权无法回收,[110]否定借款合意的效力会避免纷争的产生;但贷款人愿意提供借款以帮助借款人的,不在此限。而在贷款人方面,借款合同的债务显然无法到达“贷款人丧失资力仍要提供借款”的强度,此种情形并不在借款合同的拘束力范围之内。
(二)借款人的义务
1、“借款义务”
【74】如果承认借款合意的诺成效力,则会对当事人产生拘束力,原则上不得任意解除合意。[111]由此,借款人就需要承担维持借款人地位的义务;本文称之为“借款义务”。
【75】学说上,肯定借款义务的观点认为,在附利息的借款场合,若借款人未受领借款,也应在清偿期到来时给付约定利息;否定说则认为,既然借款人可以在清偿期到来前任意清偿而不需要承担之后的利息,那么在受领借款前当然也可以停止借款。需要说明的是,无论是肯定说还是否定说,都是基于肯定诺成借款合意的效力的。[112]
【76】从法性质上看,肯定说所理解的借款义务指的是借款人“受领借款”的义务,而否定说所理解的借款义务更多的指向合同的拘束力。在本文的立场上,诺成的自然人借款的借款人还款义务自合意达成时就发生了,受领会被维持借款人地位的合同义务所吸收,因此本文对借款义务的理解与否定说相同。
【77】实际上,无论肯定说还是否定说,在法律效果层面是接近的。否定说也认为,即使借款人在受领借款前有任意解除的权利,仍然需要承担损害赔偿责任,[113]只是并非当然以约定的利息等为赔偿对象。[114]
【78】按照《民间借贷司法解释》(二次修正)第30条的规定,在没有特约的情况下,自然人借款中的提前清偿是构成有效清偿的。这就意味着,当借款人资金需求已满足而无须维持借款人的合同地位时,借款人有权解除借款合同。由于借款合同有继续性合同的特征,若将合意的效力视为连续的过程,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的就是合意后的借款人任意解除权,也应适用于借款人尚未受领借款的场合。
【79】问题在于,若贷款人为提供借款而产生资金调配方面的成本,借款人任意解除借款合同可能会造成贷款人的损失。对此,日本民法第587条之2第2项后段规定了借款人的损害赔偿责任。对此,学者指出,该损害赔偿责任并非债务不履行的损害赔偿,而是基于合同解除的损害赔偿。[115]
诺成借款合意达成后,借款人的合同上义务为返还借款,违反借款义务逻辑上并不会产生违约责任。因此,上述对于损害赔偿法性质的观点值得赞同,此时应有《民法典》第566条的适用。[116]
【80】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借款义务的存在与否是诺成的自然人借款与在先借款合意的重要差异。后者的场合,在先借款合意并不直接生成借款合同,因此借款人并不承担借款义务;而当事人采取诺成方式时,合意会导致当事人合同上权利义务的发生,借款人也将承担借款义务。[117]
2、还款义务的发生时点
【81】本文的立场上,作为典型合同的自然人借款的要物性扩张至还款义务的要物性。而在诺成自然人借款的场合,要物性已经被当事人的合意所否定,因此借款人的还款义务应当自合意达成时即发生。
【82】有观点认为,诺成的消费借贷中的借用人的返还义务发生于标的物交付时。学者指出,上述观点的前提是将消费借贷作为“以物的返还债务的发生为目的”的契约类型。[118]但是,自然人借款是较为典型的“债务人发起型”合同,[119]起点是借款人的主观需求。就此而言,自然人借款合同也具有获得特定数量资金的利用的目的。这样的话,标的物交付是为了促进使用利益的获得,与返还并不处于同一逻辑层次。
【83】因此,诺成的自然人借款场合,贷款人提供贷款的义务与借款人返还借款的义务都自合意时发生。对于贷款人尚未履行提供借款的义务就请求借款人返还借款的情形,学说上认为可以将借款人的返还债务视为附停止条件,贷款人交付借款时停止条件成就。对此,批判的观点认为,若在法律构造上认为返还债务附停止条件,则与承认返还义务发生于借款交付时无异。[120]
实际上,针对贷款人的履行请求,借款人可以就贷款人未提供借款主张同时履行抗辩权。同时履行抗辩是以合同债务的牵连性为前提的,但在非对待给付及非双务合同的场合也存在同时履行抗辩的适用。[121]同时履行抗辩是维持当事人之间利益公平的机制,[122]若贷款人可以在未提供借款时就获得款项的返还,这显然是违反公平观念的,而准用《民法典》第525条规定的同时履行抗辩就可以避免不公平的结果。
【84】当然,如果认为诺成的自然人借款中的借款人还款义务发生于受领借款时,则可以避免上述问题的发生。但是,诺成的合意已经否定了要物性,此时的法解释无法基于要物的构造而展开。
证明责任
【85】由于实务立场并没有直接承认诺成的自然人借款合同,因此贷款人基于合同请求借款人返还本金或清偿本息的场合,贷款人须首先就“借贷事实”进行证明。
(一)贷款人的举证
【86】对此,《民间借贷司法解释》(二次修正)第16条第2款规定了法院审查的要素,包括“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
【86a】除了以上因素,对于借款是否真实存在,“双方当事人的年龄和文化程度”也会被法院纳入考量的范围。[123]
【87】同一当事人在另案中被认定存在现金借款的情形,法院据此认为贷款人具有相似金额的出借能力,从而认定借款关系成立。[124]若贷款人的资力明显不足,法院会因此认定借款事实未发生。[125]
【88】若当事人存在转账的交易习惯,但贷款人就某笔借款主张采取了大额现金交付的方式,法院会倾向于认定借款事实未发生。[126]
【89】当事人之间若存在合伙等基础关系,法院会对期间产生的转账等金钱往来进行较为严格的审查。若贷款人无法证明特定借款独立于经营活动,则会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127]当事人之间的情侣等情感关系也会影响法院对交易习惯的判断。[128]在是否存在借款关系的问题上,若公司股东做出不利于公司的证言,法院会认为该证言的“可信度较高”。[129]
【90】《借款协议》与银行转账凭证的相互印证是证据链形成的重要因素。[130]而当事人一方个人的资金往来记录无法作为有效的证据。[131]
(二)无书面借款合同的特别规定
【91】对于缺乏借据等书面证据的情形,《民间借贷司法解释》(二次修正)第17条规定,贷款人可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诉讼,借款人可反证转账系基于其他法律关系。基于反对解释,法院重视的是借款的实际交付,存在款项提供的事实会被推定存在借款关系。
【92】无借据的场合,转账记录就会成为最重要的证据之一。若当事人之间存在多笔转账记录,部分有对应的书面借据,部分则没有;法院倾向于认定上述转账均为借款。[132]可见,交易历史对法院认定借款事实存在有积极的作用。而若转款凭证附言上载明借款,借款人无法提供反对证据的,法院会认定存在借款事实。[133]
【93】对于贷款人主张的金额超过千万的借款,法院认为如此金额的借款却没有书面借据等“不符合双方交易习惯以及生活常理”,因此否定存在借款提供的事实。[134]
注释:
[1] 谢鸿飞、朱广新主编:《民法典评注合同编·典型合同与准合同1》,中国法制出版社2020年版,第470页(胡旭东执笔)。
[2] 参见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释义》,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477页。
[3] 参见魏耀荣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释论(分则)》,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196页。
[4] 参见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释义》,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477页。
[5] 参见刘勇:《<民法典>第680条评注(借款利息规制)》,载《法学家》2021年第1期,第186页(边码69)。
[6] 参见崔建远主编:《合同法》,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419页(王轶执笔)。
[7] 参见胡康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341页。
[8] 参见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释义》,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476-477页。
[9] 参见林洹民:《预约学说之解构与重构》,载《北方法学》2020年第4期,第27页。
[10] 参见[日]佐久間毅:《民法の基礎1 総則》,有斐閣2005年版,第182页。
[11] 参见魏耀荣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释论(分则)》,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196页。
[12] 参见黄茂荣:《买卖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6页。
[13] 关于典型契约的“多层次性质决定”,可参见[日]小粥太郎:《典型契約の枠組み》,载《法律時报》86巻1号,第48-49页。近来也有学者基于个别有名合同开始讨论和反思典型合同的性质识别与体系定位。参见唐波涛:《承揽合同的识别》,载《南大法学》2021年第4期,第50-51页。
[14] 诺成的借款合同为“无名合同”,这是过去日本通说的立场。参见[日]野澤正充:《消費貸借?利息》,载《法学セミナー》623号(2006年),第89页。
[15] 《民法典》第890条前段规定保管合同“自保管物交付时成立”,后段规定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的但书。但书的存在,使得第890条成为较为典型的任意性规范。第679条将原《合同法》规定的生效要件改为成立要件,目的之一就是要与无偿保管合同的表述保持一致(参见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释义》,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477页)。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没有迹象表明立法机关有意保持两者的差异(原《合同法》的规定就是如此)。基于“制度竞合”,解释论上认为第679条存在类似第890条的但书也是可能的。
[16] 有研究指出,罗马法上要物的消费借贷仅限于无偿的情形。参见[日]幾代通、広中俊雄编集:《新版注釈民法(15)債権(6)》,有斐閣1996年版,第13页。而对于约定将来进行消费借贷交付的情形,若以要式口约做成,罗马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承认其诉请可能的。参见[日]山根聡恵:《ドイツ民法制定時における消費貸借の法的性質をめぐる議論について》,载《熊本法学》148号(2020年),第64页。
[17] 对我国民法影响巨大的德国民法在2002年债法现代化法生效之前,消费借贷也采要物合同。
[18] 参见张金海:《论要物合同的废止与改造》,载《中外法学》2014年第4期,第1018页。
[19] 参见[日]森田宏樹:《債権法改正を深める》,有斐閣2013年版,第198页。
[20] 参见林洹民:《预约学说之解构与重构》,载《北方法学》2020年第4期,第27页。
[21] 参见张金海:《论要物合同的废止与改造》,载《中外法学》2014年第4期,第1020页。
[22] 参见朱庆育:《民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41-142页。
[23] 参见[日]山本敬三:《民法講義IV-1·契約》,有斐閣2005年版,第330页以下。
[24] 参见[日]高橋清徳:《関係の無償性と対象の無償性》,载[日]林信夫、佐藤岩夫編:《法の生成と民法の体系:無償行為論?法過程論?民法体系論》,創文社2006年版,第11页。
[25] 《民法典》立法参与者对第679条立法政策的解释,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之前原《合同法》立法参与者的“释义”重合的。参见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释义》,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477页;胡康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341页。
[26] 对于“商事意图的自然人借款”,除了将其视为自然人借款的子类型(边码8),还可以将其看作是“非典型”的自然人借款,是无名合同的一种;而将民法典中规定的、作为典型合同的自然人借款限定为具有互助性质的情形。另外,“商事意图”的用语表现的是借款人的主观动机对行为类型认定的影响。由于动机的多样性,本文没有采取诸如“商事目的”等表达,避免“动机”与“目的”的术语纠缠。
[27] 除了订立书面借款及担保合同,借款人往往还被要求提前出具书面收款证明。可参见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鲁民终574号民事判决书。
[28] 如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黑06民初5号民事判决书。
[29] 参见[日]渡辺達徳:《要物契約の諾成化》,载《法学セミナー》679号(2011年),第28页。
[30] 如王建文:《论我国民间借贷合同法律适用的民商区分》,载《现代法学》2020年第1期,第140-142页。
[31] 数额并不是绝对的区分标准,仍然要结合借款人的缔约目的进行综合判断。若自然人借款是为了支付彩礼,即便数额较大,也应当是民事自然人借款。
[32] 若借款目的在于从事日常耕作,则为民事自然人借款,可参见黑龙江省龙江县人民法院(2021)黑0221民初2092号民事判决书。而若借款的目的在于周托班资金周转,即使数额仅为3000元,也应构成商事意图的自然人借款,可参见河南省修武县人民法院(2021)豫0821民初838号民事判决书。
[33] 如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苏09民再182号民事裁定书。
[34] 在商事意图的自然人借款中也有提供借款这一事实对象,因此本部分有关借款提供的论述也适用于商事意图的自然人借款,所引用的实务案例也兼有两种类型的自然人借款。
[35] 参见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解读》(上册),中国法制出版社2020年版,第729页。
[36] 广东省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粤08民终2059号民事判决书。
[37]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赣民终272号民事判决书。
[38]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赣民终261号民事判决书。
[39] 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苏09民终146号民事判决书;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苏04民终4644号民事判决书。
[40]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浙民再355号民事判决书。
[41] 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冀06民终5812号民事判决书。
[42] 河南省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豫11民终2674号民事判决书。
[43] 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鲁02民终1109号民事裁定书。
[44] 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申1756号民事裁定书。
[45] 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苏13民终2505号民事判决书。
[46] 朱庆育:《民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04页。
[47] 参见[日]山本敬三:《民法講義IV-1·契約》,有斐閣2005年版,第72-73页。
[48] 日本判例的立场就是如此。参见[日]加賀山茂:《契約法講義》,日本評論社2007年版,第413页。
[49]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2015)秦民初字第2425号民事判决书。
[50] 实务中有以网络平台购物卡提供借款的,参见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豫08民终3453号民事判决书。也有债权人主张以实体购物卡提供借款的例子,参见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豫01民终16457号民事判决书。
[51] 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鲁02民终1130号民事裁定书。
[52] 如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鲁民再381号民事判决书。
[53] 参见闵遂赓:《涉出借银行账户纠纷的法律适用》,载《人民司法(应用)》2017年第19期,第87页,
[54] 参见[日]中田裕康:《契約法》,有斐閣2017年版,第347-348页。
[55] 参见杜万华主编:《最高人民法院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理解与使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167-168页。
[56] 河南省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豫09民终2809号民事判决书。
[57] 参见[日]中田裕康:《契約法》,有斐閣2017年版,第352-354页。实务中也存在这样的情形,可参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分院(2021)新40民终2314号民事判决书。
[58] 江苏省射阳县人民法院(2019)苏0924民初5093号民事判决书。
[59] 参见解亘:《冒领存款纠纷背后的法理——王永胜诉中国银行南京河西支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案评析》,载《浙江社会科学》2013年第2期,第85页。
[60] 我国民法上没有明确的“清偿的提供”概念,但学说上有类似的表达,可参见王洪亮:《债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29页。关于“清偿的提供”,可参见[日]中田裕康:《債権総論》,岩波書店2020年版,第355页以下。
[61] 最三判昭39·7·7民集18巻6号1049頁。此时,利息的起算点是另外的问题。如果没有特别约定,应自票据到期日起算。
[62] 德国民法曾使用“消费借贷的约束”来指称这样的情形。参见[日]山根聡恵:《ドイツ民法制定時における消費貸借の法的性質をめぐる議論について》,载《熊本法学》148号(2020年),第75页。
[63] 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辽02民终5876号民事判决书。
[64] 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晋01民终204号民事判决书。
[65] 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晋01民终984号民事判决书。
[66] 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9)津02民终4156号民事判决书。
[67] 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申3322号民事裁定书。下级法院也有同样的表达,如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豫01民终17067号民事判决书。
[68] 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申4338号民事裁定书。
[69] 参见[德]梅迪库斯:《德国债法分论》,杜景林、卢谌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228页。
[70] 参见林洹民:《预约学说之解构与重构》,载《北方法学》2020年第4期,第23页。
[71] 参见陆青:《<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2条评析》,载《法学家》2013年第3期,第120-121页。
[72] 参见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释义》,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80-81页。
[73] 王利明:《民法典合同编通则中的重大疑难问题研究》,载《云南社会科学》2020年第1期,第81页。
[74] 参见陆青:《<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2条评析》,载《法学家》2013年第3期,第115页。
[75] 参见[日]森田宏樹:《債権法改正を深める》,有斐閣2013年版,第213-214页。
[76] 参见朱庆育:《民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29-130页。
[77] 参见[日]内田貴:《契約の時代》,岩波書店2001年版,第90-91页。
[78] 参见[日]潮見佳男:《不法行為法Ⅰ》,信山社2009年版,第121页。
[79] 参见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解读》(上册),中国法制出版社2020年版,第729页。
[80] 参见谢鸿飞、朱广新主编:《民法典评注合同编·典型合同与准合同1》,中国法制出版社2020年版,第463页(胡旭东执笔)。
[81] 由于与诚实信用原则的关联,缔约过失责任被认为具有广泛的射程,“对各种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缔约过失行为其皆有适用之余地”。孙维飞:《<合同法>第 42 条(缔约过失责任)评注》,载《法学家》2018年第1期,第180页(边码3)。
[82] 陈丽苹、黄川:《论先契约义务》,载《中国法学》1997年第4期,第44页。
[83] 参见[日]幾代通、広中俊雄编集:《新版注釈民法(15)債権(6)》,有斐閣1996年版,第36页。
[84] 参见[日]中田裕康:《債権総論》,岩波書店2020年版,第718-719页。
[85] 章正璋:《对我国现行立法合同成立与生效范式的反思》,载《学术界》2013年第1期,第140页。
[86] 参见尹飞:《合同成立与生效区分的再探讨》,载《法学家》2003年第3期,第124页。
[87] 参见姜战军:《合同的成立与效力若干问题研究》,载《郑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6期,第79页。
[88] 参见王琦:《作为民法释义学独立范畴的法律行为效果》,载《人大法律评论》2020年第1辑,第151-155页。
[89] 广东省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云中法民二终字第246号民事判决书。
[90] 如云南省丽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云07民终758号民事判决书;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浙10民终2610号民事判书。
[91]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19)渝民再257号民事判决书。
[92] 这样的状况并不罕见,有的合议庭也有不止一次的错误表述。如陕西省咸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陕04民终1333号民事判决书;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7)鄂28民终1660号民事判决书;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7)鄂28民终1320号民事判决书。
[93] 如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申3322号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申369号民事裁定书。
[94] 广东省吴川市人民法院(2020)粤0883民初2834号民事判决书。
[95] 参见[日]森田宏樹:《債権法改正を深める》,有斐閣2013年版,第207页。
[96] 参见[日]森田宏樹:《債権法改正を深める》,有斐閣2013年版,第209页。
[97] 参见[日]森田宏樹:《債権法改正を深める》,有斐閣2013年版,第210页。
[98] 类似的观点可参见张谷:《借款合同:诺成契约还是要物契约?》,载龙翼飞主编:《民商法理论与实践》,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第226页。
[99] 参见[日]中田裕康:《契約法》,有斐閣2017年版,第346页。
[100] 对于借款合同,学说上有重视要式性而非要物性的观点。参见张金海:《论要物合同的废止与改造》,载《中外法学》2014年第4期,第1020页。
[101] 将相关签字、盖章理解为强制性规定的观点,可参见朱广新:《书面形式与合同的成立》,载《法学研究》2019年第4期,第69-70页。
[102] 参见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解读》(上册),中国法制出版社2020年版,第288页。
[103] 金融机构借款的场合,根据《民法典》第673条,借款人不按照“约定用途”使用借款的,会丧失期限利益。若金融机构借款的约定用途不包括“转贷”,则此时应排除第545条第2款的适用。
[104] 参见《日本法务省法制審議会民法(債権関係)部会资料》44,第31页。载日本法务省网站https://www.moj.go.jp/content/000100818.pdf,2021年10月8日访问。
[105] 参见张谷:《借款合同:诺成契约还是要物契约?》,载龙翼飞主编:《民商法理论与实践》,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第226页。
[106] 参见[法]Grimaldi, Michel:《恵与と契約 : 一般法に対する例外》,平野裕之译,《慶應法学》39号(2018年),第60-62页。
[107] 参见[德]克里斯蒂安·冯·巴尔、[英]埃里克·克莱夫主编:《欧洲私法的原则定义与示范规则》(第4卷),于庆生等译,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1344页。
[108] 赠与人的任意“撤销”实为任意“解除”;日本民法2017年修正案就将赠与人的“撤回”改为了“解除”。撤销针对的是单个意思表示,而合意达成的合同则为解除的对象。对此,可参见江朝国:《保险法基础理论》,瑞兴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版,第286页。
[109] 关于合同的“现实类型”,参见[日]石川博康:《典型契約と契約内容の確定”,载[日]内田貴、大村敦志編:《民法の争点》,有斐閣2007年版,第238页。
[110] 目前我国法上并没有体系性的“个人破产”制度,深圳等地已经开始局部的探索。但“丧失资力”的情形不限于个人破产,可结合具体情形予以判断。
[111] 参见韩世远:《合同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105页。
[112] 参见[日]森田宏樹:《債権法改正を深める》,有斐閣2013年版,241页。
[113] 参见[日]商事法務编:《民法(債権関係)の改正に関する中間試案の補足説明》,商事法務2014年版,第348页。
[114] 参见[日]大村敦志、道垣内弘人编:《解説民法(債権法)改正のポイント》,有斐閣2017年版,第461页。
[115] 参见[日]中田裕康:《契約法》,有斐閣2017年版,第352页。
[116]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第566条第1款后段规定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应不限于“已经履行”的场合。“尚未履行”的情形中,若相对人因解除而遭受损失,应有权请求解除合同的当事人一方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117] 参见[日]森田宏樹:《債権法改正を深める》,有斐閣2013年版,第251-252页。
[118] 参见[日]森田宏樹:《債権法改正を深める》,有斐閣2013年版,第210页。
[119] 参见[日]鎌野邦樹:《金銭消費貸借―法的性格を中心に”,载[日]安永正昭·鎌田薫·能見善久監修:《債権法改正と民法学Ⅲ·契約(2)》,商事法務2018年版,第223页。
[120] 参见[日]森田宏樹:《債権法改正を深める》,有斐閣2013年版,第208页。
[121] 参见崔建远:《履行抗辩权探微》,载《法学研究》2007年第3期,第50-52页。但在同时履行抗辩权扩张的边界方面,学说上存在一定的分歧。对此,可参加王洪亮:《<合同法>第66条(同时履行抗辩权)评注》,载《法学家》2017年第2期,第166页(边码13)。
[122] 参见[日]潮見佳男:《新債権総論I》,信山社2017年版,第301页。
[123]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21)京民申6583号民事裁定书
[124] 陕西省渭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陕05民终2338号民事判决书。
[125]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闽02民终6054号民事判决书。
[126] 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申1227号民事裁定书。
[127]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20)新民申2315号民事裁定书。
[128] 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湘10民终3005号民事判决书。
[129] 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22)藏民申78号民事裁定书。
[130]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闽02民终3817号民事判决书。
[131] 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申2280号民事裁定书。
[132] 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申4762号民事裁定书。
[133]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黑10民终1116号民事判决书。
[134] 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申3475号民事裁定书。
- 朱庆育、高圣平总编,杨巍著:中国民法典评注之规范集注(第1辑):诉讼时效·期间计算
- 刘青文译:评注的勃兴与教科书的式微——对二十世纪德国法学文献形式的15项观察
- 解亘:《民法典》第590条(合同因不可抗力而免责)
- 南京大学天同法典评注工作坊第十九期(闭门会议)
- 叶名怡:《民法典》第157条(法律行为无效之法律后果)评注
- 李承亮:《民法典》第1184条(侵害财产造成财产损失的计算)评注
- 王洪亮:《民法典》第538条(撤销债务人无偿行为)评注
- 武亦文:《民法典》第410条(抵押权的实现)评注
- 武亦文:《民法典》第420条(最高额抵押权的一般规则)评注
- 南京大学天同法典评注工作坊第十七、十八期(闭门会议)
- 辛正郁:中国法典评注中的律师——为何、由何与如何
- 金晶:请求权基础思维——案例研习的法教义学“引擎”
- 姚明斌:《民法典》违约责任规范与请求权基础
- 吴香香:中国法上侵权请求权基础的规范体系
- 吴香香:请求权基础视角下《民法典》人格权的规范体系
- 吴香香:民法典编纂中请求权基础的体系化
- 吴香香:请求权基础视角下《民法典》的规范类型
- 南京大学天同法典评注工作坊第十六期(闭门会议)
- 贺剑:《民法典》第1060条(日常家事代理)评注
- 南京大学第二届天同法典评注研讨会会议综述
- 李建星:《民法典》第807条(建工价款的优先受偿权)评注
- 朱庆育:法律评注是什么?——《中国民法典评注·条文选注》代序
- 南京大学第二届天同法典评注研讨会:评注方法论
- 杨巍:《民法典》第195条评注之二(起诉、其他中断事由)
- 杨巍:《民法典》第195条评注之二(起诉、其他中断事由)
- 杨巍:《民法典》第195条评注之一(诉讼外请求、义务承认)
- 南京大学天同法典评注讲座(第八期)&工作坊(第十四、十五期)
- 王立栋:《民法典》第641条(所有权保留买卖)评注
- 卜元石:法律知识的集成与法典时代的民法教义学研究
- 姚明斌:悬赏广告“合同说”之再构成 ——以《民法典》总分则的协调适用为中心
- 姚明斌:《民法典》第499条(悬赏广告)评注
- 尚连杰:《民法典》第962条(中介人的如实报告义务)评注
- 于飞:《民法典》实质债法总则的确立与解释论展开
- 纪海龙:世行营商环境调查与中国动产担保交易法
- 南京大学天同法典评注工作坊(第十三期)
- 尚连杰:《民法典》第501条(合同缔结人的保密义务)评注
- 南京大学天同法典评注讲座(第六、七期)&工作坊(第十一、十二期)
- 南京大学天同法典评注讲座(第五期):法律评注、法教义学与法律思维 会议实录
- 南京大学天同法典评注讲座(第五期)
- 刘勇:《民法典》第680条评注 (借款利息规制)
- 王天凡:《民法典》第496条(格式条款的定义及使用人义务)
- 杨巍:《民法典》第194条(诉讼时效中止)
- 杨巍:《民法典》第192条、第193条(诉讼时效届满效力、职权禁用规则)
- 南京大学天同法典评注工作坊(第九期、第十期)
- 翟远见:《民法典》第160条(附期限法律行为)
- 姚明斌:论中国民法评注之本土化
- 娄爱华:意大利民法典评注的撰写——以三个条文为切入点的观察
- 朱晔:日本民法注释的演变对中国的启示
- 卜元石:德国法律评注文化的特点与成因
- 南京大学天同法典评注讲座(第四期)
- 季若望:智能汽车侵权的类型化研究——以分级比例责任为路径
- 茅少伟:民法典编纂视野下物权变动的解释论
- 天同法典评注工作坊(第八期)
- 吴香香:请求权基础思维及其对手
- 吴香香:《民法典》第598条(出卖人主给付义务)
- 中国民法典评注写作指南(第1版)
- 天同法典评注工作坊(第七期)
- 姚明斌:《合同法》第113条第1款(违约损害的赔偿范围)
- 黄喆:《合同法》第261条(工作成果的交付与验收)
- 天同法典评注工作坊(第六期)
- 《民法典》评注写作规划调整与评注单元划分
- 金晶:《合同法》第158条(买受人的通知义务)| 法典评注
- 胡东海:《合同法》第402条(隐名代理)
- 郝丽燕:《合同法》第167条(分期付款买卖)
- 天同法典评注工作坊(第五期)
- 天同法典评注工作坊(第四期)
- 赵文杰:《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法定解除)
- 贺栩栩:《合同法》第40条后段评注(格式条款效力审查)
- 姚明斌:《合同法》第114条(约定违约金)
- 杨芳:《合同法》第49条(表见代理)
- 苏永钦:评注作为法教义学的工具 天同法典评注讲座(第二期)实录
- 贺剑:《合同法》第54条第1款第2项(显失公平合同)
- 纪海龙:《合同法》第48条(无权代理)
- “法典评注:比较观察与本土经验”研讨会会议综述
- “法典评注:比较观察与本土经验”理论研讨会议程&天同法典评注讲座(第三期)
- 朱庆育:《合同法》第52条第5项
- 法典评注讲座(第二期):评注作为法教义学的工具
- 天同法典评注工作坊第三期&法典评注讲座第二期
- 辛正郁 朱庆育:民商辛说改版暨法典评注开篇
- 实录:天同法典评注讲座(第一期)
- 致辞:在天同法典评注讲座(第一期)上
- 天同法典评注讲座(第一期)| 吴从周:公序良俗原则的具体化——暴利行为的民法规制
- 天同法典评注工作坊(第二期)
- 吴香香:《物权法》第245条(占有保护)
- 吴香香:《合同法》第142条(交付移转风险)
- 写意评注:中国民法典评注缘起、功能及写法
- 天同法典评注工作坊(第一期):法典评注是什么?
- 章豪:《民法总则》第10条后段(习惯作为民法法源)
- 朱庆育 辛正郁:法典评注的手账与情怀
- 致辞:在捐赠设立“南京大学法典评注研究基金”签约仪式上
- 北京市天同律师事务所捐赠签约仪式在南京大学举行
- 徐涤宇:《合同法》第80条(债权让与通知)
- 庄加园:合同法第79条(债权让与)
- 叶名怡:《合同法》第122条(责任竞合)
- 王洪亮:《合同法》第66条(同时履行抗辩权)
- 杨代雄:《合同法》第14条(要约的构成)
- 孙维飞:《合同法》第42条(缔约过失责任)
- 翟远见:《合同法》第45条(附条件合同)
- 金晶:《合同法》第111条(质量不符合约定之违约责任)
- 肖俊:《合同法》第84条(债务承担规则)
转载请注明来自金华市宝吉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本文标题:《刘勇:《民法典》第679条(自然人借款合同的成立)评注 | 法典评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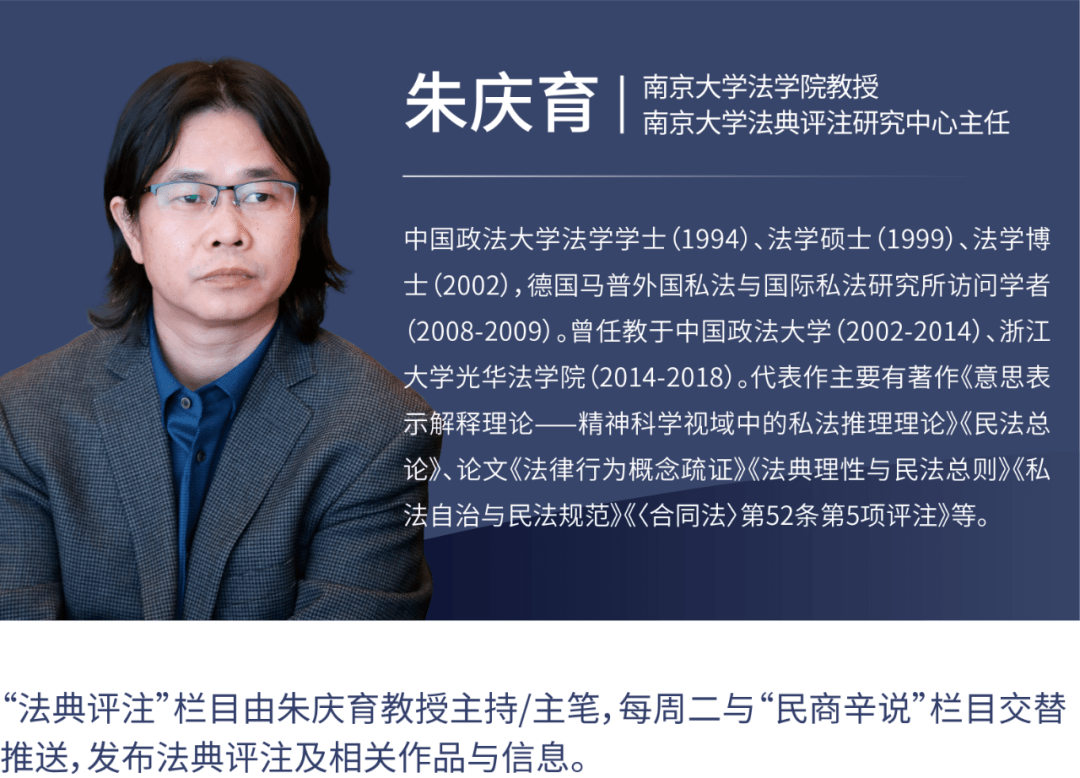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